2023年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建院100周年大喜的日子,回顾我们父子两代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关系,感慨万千。父亲1955年来到河南大学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凡33年,被誉为文学院四老之一;我是1985年来到文学院至2007年退休,共22年,我们父子在文学院工作合计55年,而且都教过先秦文学,先后都担任过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可以说与文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故想说几句心里话来表达我的心情。

一、父亲的教学
父亲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花间集注》《戏曲丛谭》及多篇高质量论文晋升为教授。父亲重视科研,更重视教学,他常说:上好一节课,如同打好一仗,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而要上好每一节课,最关键的是必须有自己的新发现、新创造。他说:在北京东北大学任教时,有一天气候非常恶劣,漫天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老师们都在教员休息室取暖。上课铃响了以后。父亲要去上课,老师们都说:华先生不用去了,这天没人来上课。父亲说:你们那个班可能没人来上课,我的班不一定没有人来上课。父亲来到教室,发现全班30多名同学一个也不少,都在等着上课。大家都认为不上华先生的课是一大损失,所以,学生从来都不缺席华先生的课。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你的课能吸引住学生呢?父亲说:上课最关键的是不能照本宣科,学生手里有教材,你照着教材念一遍,学生会能满意?你讲的课一定要以教材为基础,又高于教材,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才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而且你的新观点,扩展起来就是一篇篇学术论文,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喜欢你的课了,而且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水平,为日后的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讲课内容丰富和富于创新是父亲讲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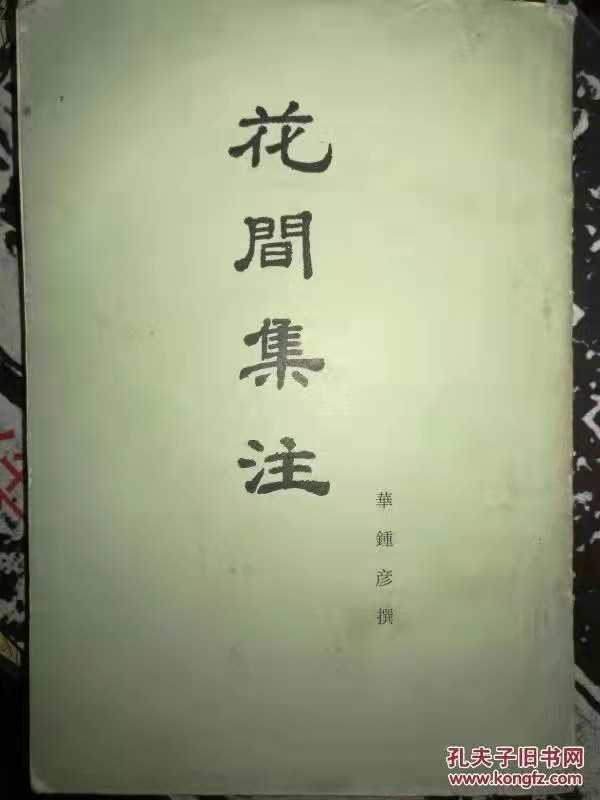
来到河南大学之后,父亲更是非常重视课堂教学。当时许多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囿于讲课的习惯及知识面所限,只能讲一部分内容,例如有些人对先秦的内容非常熟悉,但是对汉魏六朝就比较陌生,无法胜任汉魏六朝的教学工作。父亲是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唯一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的教师,一讲就是一个学期,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被当时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付钢誉为“明星教授”。六十年代初期,郑州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严重不足,父亲和高文教授等轮流去郑州大学上课,编写教材,亦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有些学生与父亲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郑州大学领导亲自宴请河南大学的领导,希望能把父亲等四位教授调到郑州大学,遭到河南大学领导的严词拒绝,说饭可以不吃,人一个也不能给你。父亲上课非常注重板书,一手漂亮的粉笔字,繁体竖排,自右向左书写。黑板写满了,从右向左一手擦,一手写,许多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手“绝技”的学生都鼓起掌来。而且,父亲教学有时候也是充满了诙谐和智慧,例如他在给中文系七八级讲《诗经·豳风·七月》第八章“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句时说:“万岁之声呱耳,而岁不见一日之增长也。”其中的含义不言自喻,引起全场同学一片笑声。
长期的教学实践,使父亲形成了严谨的课堂教学语言。文学院已故教授白本松先生曾经说过:我来到中文系后把所有老师的课我都听了一遍,河大就是河大,每个老师的讲课都很有特点。有的老师讲课喜欢铺张扬厉,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生动异常。有的老师上课情绪高涨、激情澎湃,从教室这头走到教室的那头,边走边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华先生的课是开门见山,细声慢语,娓娓道来,看似平平淡淡,实际上是内涵极为丰富,句句都有深刻的含义,都有学生值得深思的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个“废字”。有毕业生回忆中文系老师讲课的特点说:有些老师讲课高潮迭起,掌声不断,但是下了课发现笔记本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华先生的课平静如水,听华先生的课犹如只身进入宝山,到处都是奇珍异宝。看得学生眼花缭乱,心动目眩,都是忙不迭地记笔记,唯恐漏掉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学生翻开笔记本,看到华先生当年讲课的内容,仍感觉华先生讲的的确是内容丰富,闪烁着先生智慧的光芒,句句都有适用性和启发性。
父亲几十年来在教学上的特点,除了他的每节课都一定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外,再有一点就是,讲课内容十分丰富。讲课内容富于创造能够启迪学生创造性的思维;丰富的内容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把基础打牢,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父亲在讲《诗经·豳风七月》时,为了让学生们理解《七月》使用的两种不同的历法,在黑板上画了岁星的运行轨道,这样学生对“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煭”就有了清晰的概念。当然,常年奔波在课堂上,自然也就影响了父亲在科研上的投入,以至于再也没有像《花间集注》《戏曲丛谭》这样的著作问世。晚年,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心做一部《诗经汇通》。因为父亲在大学期间已经打通了文字、音韵、训诂,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他把做《诗经汇通》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文学遗产》马上予以发表。可惜天不随人愿,疾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未能完成《诗经汇通》成为父亲最后的遗憾。
二、父亲的科研
父亲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创新,重视自己的发明创造,在科研上更是如此。没有新的观点,没有成熟的想法,他绝不下笔。
建国初期,东北师大的一位主要领导心血来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的是理工科,因此文科的职称一律降一级,教授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讲师降为助教。而且取消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父亲奉命去教苏联文学的《永不掉队》。父亲没有学过俄语,但是还是天天认真备课:葛罗巴副教授是高罗沃依连长的老师,高罗沃依是葛罗巴副教授的连长。正在这时,历史系提出来,历史系不学古代文学学生读不懂《诗经》《左传》《史记》,要求中文系派教师讲古代文学。那位领导说:历史系不学习古代文学就没法研究古代历史?还有这种说法?那好吧,你们希望谁去给你们上课?历史系的领导早就想好了,马上说:我们就希望华锺彦先生来。于是,我父亲又成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到历史系之后,父亲发现历史系既没有教材,亦没有教学大纲,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父亲废寝忘食,昼夜兼程,以极快的速度编写出一本《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系领导非常高兴,第一版就印了3000册,很快就再版了。这部《中国历史文选》最大的特点是内容非常详实,从殷墟的甲骨文,到诗经、楚辞、左传、诸子百家到近代的经典范文,应有尽有。尤为难得的是,父亲把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八股文也纳入教材中,这是同期许多历史文选都没有的,表现出父亲对学术的深刻认识和对专业的深刻理解。他十分清楚,学历史的不懂得铜器铭文,等于瘸了一条腿,寸步难行。八股文这一名词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但是真正读过八股文的却寥寥无几,所以父亲编写的《中国历史文选》出版后,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许多高校使用,以至于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又再版了一次。
文革之前,父亲每天忙于教学,无暇考虑科研工作。文革10年,父亲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自然没有条件从事科研工作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才开始进行科研工作。当时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认为“清官”不如“贪官”,在他们看来,清官帮助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延长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贪官则是天天搜刮民脂民膏,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民起义的爆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痛批了“四人帮”的谬论。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邓绍基先生曾经说过:华先生是全国第一个为清官翻案的人。
三、父亲的诗歌创作
父亲自言在北大读书时期,“颇得良师亲切指导,而以江陵曾浩然先生、瑞安林公铎先生、霸县高阆仙等教益为多。他们面讲面改,析理毫芒;口耳之教,吟咏之音,至今不忘。”“于是因时而兴,感悟而动,凡邦家大事,社会珍闻,无不纳于吟咏,见于篇章。”尤其是成为高步瀛先生的入室弟子后,学习诗词创作及其吟诵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高步瀛先生是河北霸县人,自言师从安徽桐城吴汝纶先生。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四大家之一,亦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父亲自幼就喜欢诗词,又得名师教导,“由诗至于词曲,以类相从,师友切磋,其业乃进。”。1935年冬曾仿照庾信《哀江南赋》,以“东夷未灭,何以家为”八字为韵,做《望辽东赋》,一时在东北籍老乡中广为流传。(详见《侠士行》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父亲曾经三次受到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可惜这首长篇大赋,随同父亲的大部分诗词创造都毁于丙午浩劫。

现存的诗词,大部分是父亲后来回忆起来保存下来的,小部分是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父亲认为诗词创作一定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例如现存的《侠士行》就是写1932年朝鲜人尹奉吉刺杀日本白川大将之壮举,此诗发表于1932年5月15日《大公报》。七七事变后,父亲失去了工作,每天为衣食四处奔走。曾口占一绝:“饥来驱我走风尘,哪惜穷愁久病身。一岭霜花千里月,寒光孤照板桥人。”凡家国大事,父亲多以诗词记之。如1945年光复之后,父亲仿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做《“八一五”日本投降感赋》:“一闻捷报动乾坤,狂喜惊心见泪痕。惩暴方知天有眼,藏奸应恐地无门。也因夜雨添诗兴,好对秋花倒酒樽。无怪妻孥拼共醉,十年酸苦敢轻论。”解放之后,父亲积极参加学习,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1954年,应赵纪彬先生之邀,来到河南新乡,旋即来到开封。这些都有诗歌的记载。
父亲的诗歌创作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诗关国政”,体现出父亲的家国情怀,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一贯立场。二是坚持诗歌创作与现实充分结合起来。例如1979年以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先生为团长的访华代表团来到河南,代表团在北京是由邓绍基先生接待,省文化厅提出让父亲负责接待代表团,父亲欣然从命。父亲见到吉川后得知,吉川亦是北大毕业,于是二人回忆了北大学习的情况,共同吟诵了杜甫的《登高》,平仄高低,音韵长短完全一样,吟诵后两人相视一笑。这时吉川先生提出想拜谒杜甫窑,请父亲代为向有关领导请示。有关领导说:杜甫窑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但此时杜甫窑还住有农户,院子里鸡飞狗叫猪哼哼的确不宜对外宾开放,请华先生代为婉言谢绝。父亲口占一绝:“窑湾春涨路难开,杜老遗踪锁碧苔。领会青云动高兴,明年扫径待君来。”吉川先生知道此行无望,长叹一声说:谁知道我明年能不能来呢?吉川先生于次年与世长辞,没有能拜谒杜甫窑成为他终生的遗憾。父亲做《悼念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表达对日本友人的怀念。“闻君归去我心哀,热泪催诗吊夜台。中日论交文会友,京都立教世多才。登临并影成千古,吟咏同声尽一杯。未到窑湾莫惆怅,枫青入梦待君来。”可谓情深意切矣。本世纪初,我以河南省吟诵学会会长的身份,接待了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拜谒了杜甫窑,共同吟诵了杜甫的《登高》,算是对前辈有了一个交代。
再如,父亲在诗歌创作中充分表现出他鲜明的爱憎观念,如1976年4月5日的《“四五”怒潮》,1976年10月填的词《念奴娇·粉碎“四人帮”》都是对“四人帮”的批判;1978年的《怀念朱总、贺帅》《彭大将军》《悼念陈总》等等,都是对革命前辈的歌颂与尊敬。即使有些与时政关系不大的生活琐事,也反映出父亲的善恶观念,如《论诗十首》《感遇》等等。父亲的诗词很少涉及风花雪月,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吟咏风花雪月,相反他对风花雪月也是十分熟稔,例如他有一首歌颂周总理的五言长篇排律,就用了“雪舞梅花俏,风吹松韵清”对仗十分工整,读者无不拍手称赞。
四、父亲的为人处世
我们家原籍是山东,清雍正年间被移民到东北。山东人的性格,在黑土地上又拼了十几代人,我们的先辈逐步养成了勤劳善良、勇敢顽强、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精神。父亲是一位书生,但身上仍然有着祖辈流淌的血液。在沈阳时因为看不惯日本人的骄横,把日本人痛揍了一顿只身来到北京。在长春时,让教苏联文学就教苏联文学,让讲历史文选就讲历史文选,不向困难低头。在为人处世上,父亲坚守做人的底线和良知。文革时,造反派批判父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父亲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但是让父亲去检举揭发其他老师的问题,他一个字也没有。父亲和钱天起教授关系甚好,这是源于钱天起教授对父亲工作的认可。钱天起先生主持中文系工作时,父亲最多时担任10件工作,第10件是负责中文系的计划生育工作。恰在这时,钱先生生了二女儿,父亲吃饭时说:我得行使一下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了,让钱先生注意计划生育。我们都哈哈大笑,说大可不必。1964年钱先生在开封禹王台休养,父亲去看望钱先生,做《满庭芳·吹台访钱天起教授》。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先生则是中文系所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可见父亲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提起父亲的为人,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66年的6月3号或者4号,一位中文系的学生来到我家,向父亲借5毛钱,现在想想,这个学生可能压根就没有准备还这5毛钱。父亲把桌子上的五元钱递给这位学生,说:“这是开封日报刚刚送来的稿费,你拿去用吧。”那位学生说:“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能还清呢?”父亲说:“我又没有说让你还,你好好学习就可以了。”那个学生千恩万谢地走了。大约过了两三天,就是1966年6月6日,河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位前天还是千恩万谢的学生,居然在10号楼最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腐蚀拉拢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改革开放后,家里来了一位学生,父亲请这个学生吃了一顿饭,还住了一夜。父亲问他最近看什么书?这个学生说:就看看《三国演义》。父亲说:看《三国演义》也好啊!可以搞搞元明清文学。那个学生说:哪啊?就是看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我顿时无语了。学生走后,我问父亲说:这是什么人啊?你还请他吃饭?父亲说:就是那个要借五毛钱的学生。我一听就火了,说:这样的人你理他干什么?父亲笑着说:他毕竟是学生嘛。我立马又无语了。
五、父亲的吟诵
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的吟诵。可惜那时候玩心太重,父亲什么时候得空了,而且我又在他眼前晃荡,才抓住我,教我吟诵一首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知道吟诵的重要性,开始主动向父亲请教有关吟诵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父亲去陕西参加唐诗讨论会,父亲在大会上做了重点发言,最后说:学习唐诗不能光念念就行了。学习唐诗一定要学会吟诵,说完就吟诵了几首唐诗。父亲的吟诵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会场喧闹起来,年长的来到主席台,要吟诵几首得意之作;年轻的彻底懵了,唐诗还能这样“唱”?1982年下半年唐代文学学会正式成立,父亲出任理事,并担任“唐诗吟咏研究小组”的组长,拨款300元作为活动经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吟诵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两年一次的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上,都要把唐诗吟诵作为一个专门的展示项目。父亲利用这个“小组长”的身份,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搜集各地的吟诵调。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先生说:华先生搜集吟诵调的方法就是标准的田野调查的方法。父亲千辛万苦搜集的珍贵的几十盘录音,上世纪末经赵敏俐介绍,徐健顺同志第一次来到开封,我将父亲搜集的录音,全部送给健顺了,作为对吟诵事业的支持。许多人都说,这批音响资料是现存最早最宝贵的文献了。
父亲对吟诵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更重要的是对吟诵这种传承两千多年的读书方法进行了理论研究,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父亲通过个人反复地吟诵,聆听国内其他吟诵大家的录音,与其他吟诵大家的交流,提出吟诵的12字基本规律:“平长仄短,节奏鲜明,声情并茂”,并写出了多篇文章加以论证,可以说父亲是当代传统吟诵复兴的开山鼻祖。此后虽然有许多人对什么是吟诵,吟诵的主要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都没有脱离父亲对传统吟诵基本认识的框架。尤其是父亲格律诗的吟诵,被誉为格律诗的“八大调”,称为海内独步也不为之过。华调吟诵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举一反三。学会了一首格律诗,那么同一体裁的诗歌都会吟诵了,为之“套调”,又称之“一调吟千诗”。目前,国内吟诵圈里基本上认为文的吟诵以唐调为最,诗歌的吟诵以华调吟诵为优。而唐调的吟诵与华调的吟诵都是传自吴汝纶,只不过是各有偏重罢了。

父亲患病之后,河大中文系陈信春老师、刘增杰老师、关仁训老师、李春祥老师、李博老师专程赴京探视父亲。父亲去世后,他们主持了父亲的火化工作,在此,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这里面有四点应该说一下:
1、当时在京的许多学术界的朋友都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如周振甫、徐放等人都参加了,他们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无不感到惋惜和悲痛。
2、在举行遗体告别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当遗体推往火化炉时,突然晴空一声霹雳,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不知道是谁说了句:泪飞顿作倾盆雨啊!八宝山附近积水达半尺之深,据北京人说,这个时候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是不多见的。
3、河南大学为父亲的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挽联挽帐挂满了小礼堂,几乎所有的挽联挽帐都是请河大著名书法家王刘纯先生书写的。王燕曾戏言:这是刘纯的书法展啊!
4、在追悼会开完的晚上,宋应离先生专门来到我家,深情地说:就开追悼会的规模来说,可能以后超过华先生追悼会的规模还是有的,但是为失去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而发自内心的感到悲伤,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了。
与父亲相比,我的确是乏善可言。我自1996年起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除了精心安排好课程,搞好教研室的团结之外,唯一可说的是我非常重视选修课的开设,我提出“选修课是通往科研的桥梁”,因为你要想开一门选修课,你就必须看书,研究有关的知识。在我的倡导下,古代文学教研室,每学期都开设3门选修课,是中文系开设选修课最多的教研室。此外,在继承、发扬、光大华调吟诵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了父亲对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歌行体及词的吟诵的基本吟诵方法,并有所发展。例如:父亲喜欢用一个曲调吟诵《诗经》,我则主张把《诗经》的吟诵分为正风正雅、变风变雅,他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父亲对古代文学作品十分熟稔,对吟诵把握得十分准确到位,所以任何一首古诗,他拿到手中就能吟诵。我在反复聆听父亲的音频之后,提出将父亲的古诗吟诵分为六种,便于华调古诗吟诵的学习和推广。有人说词是唱的,不能吟诵。我提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填过词,不懂得吟诵在诗词的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父亲每逢新春时都喜欢填一首[浣溪沙]或[金缕曲]以示祝贺。父亲一般都是嘴里吟着,手里写着,写好之后看着吟着改着,感觉差不多了,再抄一遍,再动个别字,一首词就填好了。所以,词的吟诵主要是用于词的创作阶段,吟诵的本身就是为了调平仄。至于词的歌唱,是在饮酒作乐时的一种娱乐的形式。不懂得词的吟诵,你就无法从事词的创作;不懂得词的歌唱,你就无法融入文人的娱乐圈,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所以词的吟诵与词的歌唱都是文人学子必备的专业技能。进而,我在反复思考之后提出,有声阅读可以分为四种方法,即朗诵、吟诵、吟唱、歌唱。这四种方法各有优长,使用的环境亦各有不同,吟诵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是按照一定的韵律和节奏充满感情的读书方式,在四种读书方法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吟诵对于青少年学习、背诵古诗词极为便捷,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在“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学会、理解了古诗词。更重要的是,华调吟诵非常适合于课堂上给学生们边讲边吟诵,将华调吟诵归结为为适合课堂教学的读书方法一点也不为之过。
也正是我掌握了韵文基本的吟诵方法,2010年元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成立时,我被推举为副理事长,2013年河南省吟诵学会成立时,被选为首任会长。2013年山东李宁千里迢迢来开封专门学习华调吟诵,之后她提出要拜我为师,犹豫再三,考虑到吟诵为口耳相传之学,如果举行了拜师仪式,他们也有了一个名分,于是我同意李宁的要求,首批收她及其他9名学生为华调吟诵第五代传人,此后又收了几批,共计有130名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吟诵爱好者成为华调吟诵的第五代传人。据学生们统计,除了西藏、宁夏、澳门等少数地区没有人传习华调吟诵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人传习华调吟诵。听过华调吟诵的达百万之众,学习华调吟诵的有10万人以上。
我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川、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广东、台湾等省市自治区做过讲座,其中仅广东省就在广州市、深圳市、湛江市、中山市做过讲座。我在全国各地做讲座,一律是公益的,不收学生一分钱;就是收徒入门,也是不收一分钱。我的理念是:在国家、人民的支持下我的吟诵事业才开展起来,我应该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推广华调吟诵来回报社会,而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牟利的工具或手段。记得第一次在深圳罗湖区图书馆做讲座时,2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走廊、讲台前都是席地而坐的都是青年男女听众,还有从香港专门来的听众。主持人许石林先生说:深圳每个周末都有许多场讲座,一般的听众都不多,最少的就几十个人。像这么多人参加的讲座,的确很少见。2017年华调吟诵成为开封市市级非遗项目,2021年华调成为黑龙江省鹤岗市非遗项目,华调吟诵越来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
为了推广华调吟诵,在河南省大象出版社王刘纯社长、赵涵副主编、孙波主任以及编辑袁俊红、邵培松等人的支持下,我先后主持出版了《基础吟诵75首》《中级吟诵61篇》《诗经诠译》(增订本)等著作,其中《基础吟诵75首》已经是第七次印刷了,《诗经诠译》创半年发行9000册的记录,可见这些书还是很受读者喜爱的。在王社长和郭孟春主任的支持下,我在大象社做了音频版的《格律诗吟诵20讲》,给《诗经》305篇全部配了华调吟诵。今年又在郭孟春主任的支持下,为义务教育一至九年级的学生出版了《中华经典—古诗词诵读》1—9册,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的许多学生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河南省轻工业大学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一个省部级的大奖(全国一共50个),濮阳油田四小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河南省10大特色学校,郑州市淮河路小学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一个省级项目,并顺利结项。还有许多学生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改变了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有人仅以推广华调吟诵就可以满足生活所需。



父亲去世之后,对我的打击之大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继承父亲的事业,推广华调吟诵是我唯一的使命。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姚小鸥师弟、张云鹏总编等人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华锺彦文集》的编选,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2016年在河南大学及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召开了华锺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关爱和书记、王文金老师都亲自与会,并做了重要发言。王文金老师还赋诗三首,请书法家王刘纯先生写为卷轴,令我十分感动。父亲来到河南在新乡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年过80的韩玉生先生、曾祥芹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下,会后准备出版一部《华锺彦先生纪念文集》,这部书虽然是挂我的名字,实际上完全是耿纪平博士、孔漫春博士两人操作成功的,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就没有这部著作的今天,在这里我向河南大学文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耿纪平博士、孔漫春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这部书的出版,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的一件事了。今年我已经满74周岁了,又身患恶疾,但我不准备向病魔屈服,在遵从医嘱,坚持服药的同时,尽可能地把我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些对于国家、社会可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但对于我的家人、对于我的朋友、对于我的学生可能有一点影响,对于我们父子曾经工作过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是一份详实的史料。是为此文,以飨读者。
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