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李嘉言先生的哲嗣之禹兄来函,通报正在编辑嘉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同时还寄来嘉言先生的《长江集新校》一书。
河南大学是我的母校,嘉言先生是我的恩师、之禹兄是我的同窗好友,无论从哪层意义上,我都应当奉上一份感念与敬意。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叙述过我第一次见到嘉言先生的情景,那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对我的人生道路却产生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我把它看作我一生中罕见的一道“灵光”, 一道从幽冥中闪现的 “灵光”:那时我还在开封一高读书,夏季的一个黄昏,我随李之禹到他家中取一点什么东西。有段时间我与之禹过从甚密,是好朋友,还曾在一起照了不少相片,是他出面邀请河南大学的外籍教师吴雪莉,一位丰硕的金发碧眼的美妇人为我们拍摄的。李家住在校外的惠济河岸边,是河南大学为教授们盖起的新宅,一律平房独院,我记得那天有些阴晦,而且已是暮霭沉沉,屋里面却显得很明亮。门里的东屋,是之禹父亲嘉言先生的书房。先生正伏案翻书,我们怕惊扰他,象小狗一样弓着身子从书房门前掠过,连正眼观看一下都没有来及。然而正是这匆匆一瞥,时间怕只有一秒左右,却在我心头停驻下来:柔和的散发出温暖的台灯,四壁满装图书的书架,散发出芬芳的笔砚,书案前若有所思的学者。我几乎听到自己心里发出呼喊,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李嘉言先生(1911-1967)
那时候听之禹讲过他的父亲李嘉言先生: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朱自清先生的助教、西南联大的讲师,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遗产》的编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了什么新书,总是先把书单寄到他们家来。一篇文章考证了楚辞中的两个字,稿费寄来100多元……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

1963年夏吴雪莉教授拍摄的照片:李之禹(右3)、吴雪莉的儿子(右2)、鲁枢元(右7)

西南联大步行团:闻一多(中间蹲者)、李嘉言(左下角坐者)
没有想到,两年后,我真的成了他的学生。不过直到那时候,开封市贫民区一个利用暑假时间去拉板车补贴家用的中学生,距离文学教授还不知有多远的距离。从那时起,23年过后,曲曲折折阴差阳错,我倒真的当上了“教授”,而且是“文学教授”。此时,我的台灯、书案、书架、“笔砚”,以及那种两袖清风,坐拥书城的感觉,真是与50年前“灵光”闪现时的情景别无二致。
1963年秋,我进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河南大学,经过50年代的大专院系调整,已由河南大学缩编为河南师大进而降级成开封师院。
俗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河南大学虽然变成了开封师院,所幸还有一个阵营可观的教授群支撑着,如任访秋、华钟彦、高文、万曼、于安澜、吴鹤九、王梦隐、郭光诸位先生,而李嘉言先生正作为中文系主任,统领着这一局面。更何况,那巍峨的中西合璧的大礼堂还在,典雅古朴的东十斋房还在。
入校后,我所住的学生宿舍在甲排房最东边的一间,紧靠铁塔湖,久经历史沧桑的开封古城墙就横亘在湖水的东岸。中文系的教室、资料室、教研室、行政办公室全在十号楼,那是一座红砖建造的四层楼,刚刚盖起不几年,是当时开封城里最高的楼房。我就是在这座楼的过道里,再次见到李嘉言先生,他正在和一位教师谈论着什么。较之那次“惊鸿一瞥”,这次是“定睛细看”了,嘉言先生高高的身量,偏瘦,有着豫北人的肤色与口音,神情庄重却又透出和善,言谈沉著而又使人感到亲切,正是我心目中的大学者的形象。
那时,嘉言先生并没有给低年级学生开课。听上面六零级的同学说,嘉言先生正在给他们讲《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已经讲了半个学期,并誉之为“楚辞专家”,那种深得名教授真传的幸福与风光溢于言表。我为了将来听嘉言先生的课提前做好准备,特地到图书馆借了《楚辞集注》,同时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白油光纸自己订了一个札记本,生吞活剥地啃读起来。后来我还在东大街的旧书摊上买到过一册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多年后在搬家中丢失了。读《骚》自然是不得要领,领会最深的只是“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中的后半句。这半句对我至今在学术的“漫漫”长途上求索不已似乎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算起来,也该归之于嘉言先生的言传身教。
后来我才知道,嘉言先生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其实并不在“楚辞”研究,也不在于他曾涉足的佛教与元朝文学,而是在唐诗研究。这是我从孙先方先生那里得知的。进入大学的第二年的冬天,中文系的师生便停课参加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开始时是“小四清”,地点在豫西巩县的黑石关镇,我所在的生产队叫“大北沟”,与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孙先方老师同住一个窑洞,我当时也就是十八九岁,第一次住窑洞,孙老师则是我第一次作为“工作队员”走进社会的引路人。孙老师其实也是一位忠厚书生,一位做学问的人,四清时住在窑洞里还看专业书,是唐诗。他告诉我开封师院中文系担负着一项国家的重点项目,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即整理改编全唐诗,而项目的主持人就是李嘉言先生。从他谈起嘉言先生的语气里,我更感觉到嘉言先生的学术地位与人品风致。
“小四清”完了是“大四清”,阶级斗争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我们的“阵地”也由豫西转移到豫东。通许县的“社教运动”几乎延续了一年,重新回到学校还未曾在教室坐稳,文化大革命便已狼烟四起,整个古老校园陷入熊熊烈焰之中。在十年浩劫的第二个年头,嘉言先生便不幸去世,享年仅5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嘉言先生与中文系的其他一些教授还不完全相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属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然而也仍然没有逃脱那场浩劫,究其原因反倒是因为他学问做得太好,太深,于是当然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后期,我和嘉言先生的次子、我的同学李之禹都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教书,有一段时间还同住在郑铁机务南段一个破旧的大院子里。之禹的姐姐之舜也曾来过这个院子,那时之舜还是位容光焕发的美女,不料她也竟英年早逝,造化令人无奈,令人伤凄。之禹先我搬出了机务南段的大院,听说与吴雪莉教授的混血女儿结了婚,又分了手,那已是后话。文革期间时常“停课闹革命”,空闲时间除了画画,我曾学做过木工,做过一只带抽屉的单门柜,至今还在郑州老家放着。还曾学着裁剪衣服,两毛钱一尺的灰棉布做了件衬衫,不合身,废掉了。有一次之禹说他有一块好看的有机玻璃,希望我为他改制成台灯,我自忖手头没有得力的工具,就没有揽下这个活,至今尚余歉意。

晚年的李之禹仍住在铁路局的家属楼里,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毕生大业。墙上悬挂的是父亲李嘉言的遗像
如今我与之禹都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他赠送的这部关于贾岛研究的《长江集新校》,为“百年河南大学国学旧著新刊”丛书之一种,是嘉言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贾岛,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一位诗人,苏东坡对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曾有“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的品评,然而对其诗歌成就的具体理解历来又褒贬不一,褒者谓之“峭拔莹洁”“意在言外”,虽善雕琢而字字精透;贬者谓之“怪癖狭窄”,“苦寒而近酸涩”。尽管褒贬不一,贾岛诗歌对于清扫大历以来绮丽浮弱的诗风功不可没,对于后人的影响也是持久悠远的。我自己在童蒙时代就知道“僧敲月下门”与“一吟双泪流”的典故,以及“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佳句。这样一位诗人,以往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充足,不但比不上元、白,甚至也比不上与他齐名的孟郊。嘉言先生的贾岛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开导先河的功绩。我有时猜想,这或许是受到朱自清、闻一多二位先生的直接点拨,因为这时他正在二位先生身边,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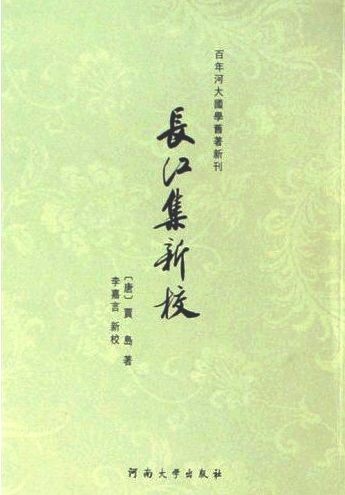
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不是我这古典文学研究的门外汉所能置喙的,令我深受感动的是前辈的治学精神。书中附录的《贾岛年谱》,连同附写的五篇相关文章,其实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共不过十万字,而嘉言先生从1936年春开题,到1941年部分发表,再到1947年付梓成书,整整用了十年时间,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四易稿成,五经寒暑,三移厥居”,况且其间正逢抗战时期,长年漂泊流转,做一位学人那需要多么强大的“定力”!校注贾岛的《长江集》,继《年谱》之后,又持续了将近十六年,而且先生临终也未能看到此书出版,这样的治学决不是如今的所谓学者专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年头,我们每个人都应对照前辈学者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多少优良学统的血脉!
“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本是贾岛哭孟郊的诗句。前辈学者身死名在,我也尝以曾经沾及先贤甘露而窃窃自喜,记得在课堂上曾向我的学生炫耀:你们知道自己与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的距离有多远?不远,中间就隔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再就是我的两位老师任访秋先生与李嘉言先生,他们都是胡、朱、闻等前辈大师的嫡传弟子。然而扪心自问,我又承继了自己老师的几多学脉?
“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每观今日之学术界,常有“落日孤舟”之叹,好在青山依在,那就是前辈学者的文字与精神,将指引我们在学术的层峰叠峦间持续地寻觅与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