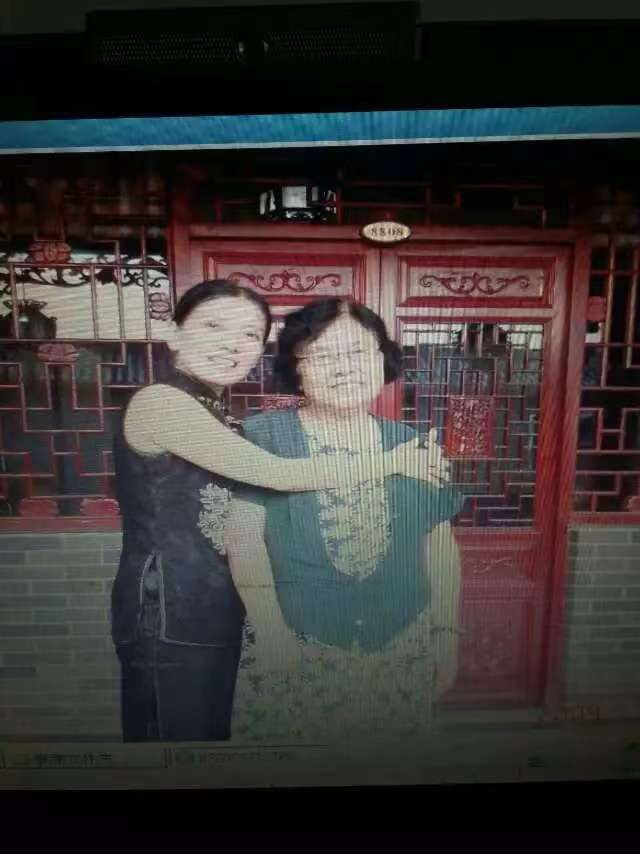两位刘老师离开我们至今,一年来,我一直无法面对这份哀痛,每每想坐下来写一点文章,总感觉轻飘飘的文字,承载不了这份哀痛与思念,导致无法写下只言片语。而现在,对我来说,依然不是能够流畅写下纪念文字的时候。
我是2005级孙先科老师的博士,在校读书那几年,两位刘老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搭建起河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宽阔坚实的学术平台,那是一个春光明媚、风光无限时代,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正如关老师说的那样,两位老师是河大现当代文学的两座灯塔。刘增杰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他给我们讲做学术要注重史料观察事物有三种角度:仰视、俯视、平视,而学术研究要选择平视的角度去看待事件、问题和人。回想起来,在第一堂课,他就为我们推开学术研究大门之后,面对浩瀚如海、迷雾般的历史和史料时,应该怎样探索指明道路,尤其是我这个硕士之前研修音乐、跨界而来的学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刘思谦老师,因为她是我导师孙先科的导师,因此,有更多的请教。我们经常到她家里,她常常会讲她自己人生故事,有时,那些故事是换了另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可能说的事情,她都会讲给我们听,有时她从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中引入女性文学研究的话题,不知不觉中引起我们对女性文学问题的思考。大约是在我读博二年级,不知哪天起,我便不再称她刘老师,而是喊她“额娘”了,这种称呼是我对她的专属,也许是因为我渐渐感到:当我因为性别而产生的困惑和问题时,她一定是那个像娘亲一样给你呵护答案的人。她以对现当代女性作家的研究,揭开历史时代、国家宗族、婚姻家庭等对女性命运的不公及压迫的秘密。以充满个人生命温度的笔端,劈开笼罩在女性命运之上的荆棘迷雾,这是何等的智慧!正是老师的一篇篇文章、讲座乃至听她平时和我们的一些女性文学话题的聊天,让我的女性意识渐渐得到觉醒、生命意识觉醒,这是在我河大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意外的收获。在生命中能遇见唤醒你生命的人,何其幸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若没遇见她,我永远不会明白那些笼罩在女性生命里的罪恶牢笼,生在牢笼而不知,打破牢笼与锁链则更无从谈起。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原本是交给孙先科老师修改的,论文打印出来后,我也交给“额娘”刘老师一份,过了几天刘老师就把稿子返回给我,打开一看:稿子从头到尾,圈圈点点,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一样。拿到这份倾注额娘心血的手稿,我有种说不清的感动。我是孙先科老师的学生,孙老师是刘思谦老师的学生,没想到导师的导师、已经76岁的她,如此认真地为我修改论文。这里面倾注了她对两代学生满腔的爱,也饱含了她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今年3月3日,母校文学院百年院庆,文学院院史馆开馆特别的日子里,我即把这份珍藏了十四年的博士论文初稿捐给了文学院院史馆。我希望后来的学子们能感受到她老而弥笃“育才不遗老骥力”的精神,领略她对我们精心培养、悉心教导的这份温暖与真情。
去年7月18日,亲爱的刘思谦老师老师离开我们,7月24日早上八点,在省人民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时,疫情正严重,她远在海外的大儿子和女儿全家都无法回国,只有小儿子小元赵池春夫妇在郑州,在省医告别会上,小元对我说:一会儿你和我舅舅还有我和玲玲咱们四人一起把我妈妈抬出来吧。到了殡仪馆,也是我们四人把她推到火化炉,那一刻,我给额娘深深鞠了三鞠躬,大声喊道:“额娘走好!”
额娘活着的时候,以她的信仰、至纯至真的品格感染我,满满的爱包围着我,有幸能够为她抬棺,并和他们一起把她推进火化炉。见过她神采飞扬,亦见到她凤凰涅槃,是我今生和她最大的缘分,一定也是上天的安排,安排我代表所有爱她的学生们为她献上一份永远的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刘增杰老师,因为疫情我们都无法送他最后一程。送别刘思谦老师时,关爱和老师在给她敬献的挽联上写到:“是大先生,笔走风雷,何须辨男儿女儿。有真信仰,言说自由,莫问它今生来生。”是的,两位刘老师,无论为人为文为学,均抵达了我辈须仰视才见的境界,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更是绵延不绝的爱,也将永远滋养我们,我们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人类正是因为爱,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