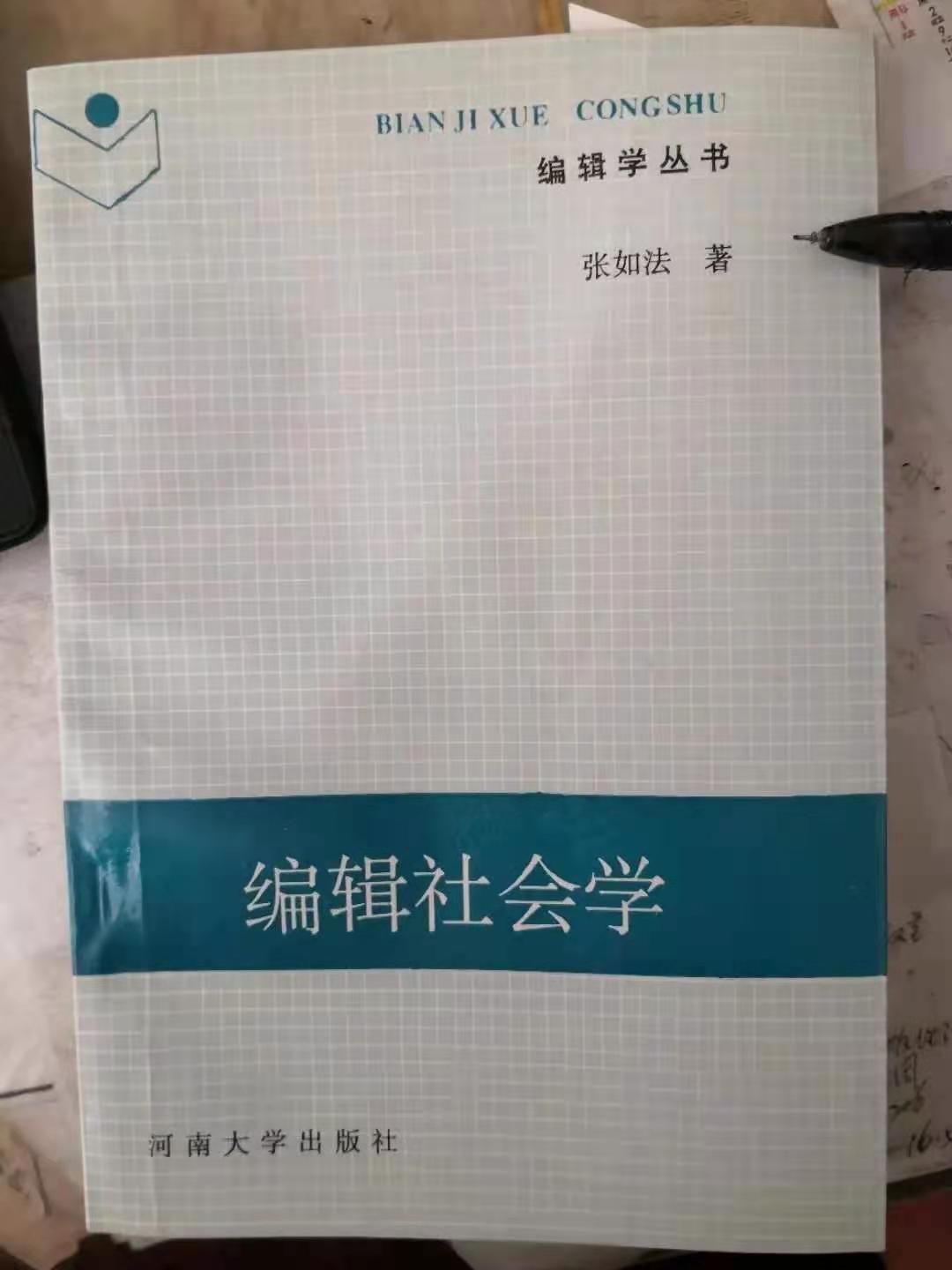
我是2020年3月20日得知先师张如法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写一篇文章,太太慌里慌张地上来说:张老师走了,昨天,3月19日在开封家中走的,是张老师的嫂子刚刚告知的,是不是真的?赶紧给徐师母打电话问问情况。
电话接通后,师母不等我说出安慰的话,便细说先师临终情况,最后还说嫂子不该把消息告诉我们,说疫情特殊时期,给大家增加麻烦。师母就是如此细心周到,像先生一样处处为他人着想。放下电话,我犹豫一两小时后,还是在编辑出版教育微信群中转发旧文《如法师》,加缀一句导语:“难抑怀念深情”。过一会儿,我忍不住又私信问询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位朋友在哪里,没想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河南南阳,只有副院长王鹏飞教授在开封。鹏飞听说张老师去世的消息,也很震惊,随即便联系院长等一行四人去张老师家中吊唁。当天,院长又汇报给河南大学前党委书记、《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前主编关爱和教授。关老师因一周前从郑州回到开封,正在隔离期内,无法走出家门。他发来微信表示哀悼,并说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张老师签发的。
先生走了,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如此孤寂地走了。我悲从中来,又手足无措。不知该为先生做点什么,此时又能做点什么。
先生撰著过一部《编辑社会学》,该书是1987年为我们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1989年初版。当时听课的是学报编辑部招收的我们三个首届编辑学研究生和十多位研究所课程进修生。我读编辑学研究生最早、最热闹也最有收获的专业课是听编辑部老师们每周三下午讨论编辑学教材编写,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收获不在于哪怕一两条专业定论,而是胡益祥先生为鼓励研究生发言而一语捅破的那句话:在编辑学道路上,导师和研究生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曾撰《因为那两句话》铭感师恩。如法师自然不是积极的讨论发言者,但他是导师中最早出版教材的。《编辑社会学》1993年再版时,我在《新闻出版报》发表一篇《<编辑社会学>再版感想》,联想到法国学者吉贝尔·米里1957年发表的《图书社会学可能吗》,我在文章中说:“从法国到中国,从1957到1989,从预言到现实,多么令人兴奋!”湖南师范大学周国清教授有一次同我谈起改革开放以来的编辑出版理论成果,他充分肯定了《编辑社会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我一直默存心中。
先生的自然生命已经终止,他的社会生命则进入下半场。那几天我正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编写相关人物条目,由此想到,张老师如果作为一个人物条目,他的定性语该如何界定呢?第三版《编写条例》规定,人物、地名、机构等条目释文开头使用的定性语是非专指性的,以归类方式说明其属性。几番思索后,我首选了“中国编辑学家”。
我第一次看到“编辑学家”一词是1994年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该报记者王衍诗写的《生命的红灯亮过之后——访编辑学家、河南大学教授宋应离》。王衍诗是我的研究生同学,我理解他的这一称谓是学生对导师的敬语,也有记者的学科敏感。但这一称名并未由此广泛而正式地流传开来。我想,在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伴随改革开放走过40余年后,以编辑学家、出版理论家、编辑出版理论家、出版经济学家、出版史家、出版史学家等为视角检视、梳理第一代编辑出版学人的理论贡献,将有利于这一学科继往开来。
张如法老师作为编辑学家的独到理论贡献就是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编辑社会学》著作。该书初版和再版都有相同的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探索编辑社会关系的书。
现代的编辑行为早已不局限于编辑改改了,现代的编辑正在和将要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丰富多样。现代信息社会已经益发离不开编辑机制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编辑的各种社会关系,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立体式格局……这一切,都使得封闭式的研究已经无法揭示编辑的“庐山真面目”。必须将编辑、编辑行为和编辑组织,放在种种社会关系中,进行开放式的考察和研究。
本书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作者期望一切有志者,能共同关心、研究编辑社会学,使其蔚为壮观。
30多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些文字,真该叹服他的理论预见性,尤其认可其“必须将编辑、编辑行为和编辑组织,放在种种社会关系中,进行开放式的考察和研究”,真让我赞佩不已。我将它理解为先生编辑社会学思想的基本主张,有此基本主张,编辑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才有理论基础。而基本主张和基本框架作为两个重要要素合成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编辑、编辑行为和编辑组织是编辑学的一般概念,现在基本通用,但30多年前首倡并予以明确,还是先人一着的。我前几年给研究生上出版行为分析选修课有多轮,充分理解了编辑出版行为的玄妙精深。因此,对《编辑社会学》2006年重印本的封面介绍文字也有更深刻的理解:“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类社会特有的编辑现象作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探讨了编辑与社会、作者、编辑、出版发行、受众五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使读者对编辑现象有更接近全貌的清晰了解,同时指导编辑行动的自由自觉。”
先生《编辑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是社会学。那时的编辑学与传播学几乎同时起步。先生的创新不是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移花接木,而是基于自己和他人的从业经验去内化,尔后倾吐哪怕并不精致、完善的思想,从而不仅与今人对话,极可能与后人对话。
《编辑社会学》1989年出版时,印数仅1000册,版权页的责任编辑项里,署名“边学”。我对这个署名非常熟悉。1992年,我的第一本专著《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出版前,由如法先生一审、责编,宋应离社长三审。两位导师分别为自己研究生的处女作承担一审、三审,现实中可能不太多吧?作为被审者我又何其荣幸。那部书的责编署名就是“边学”。我当时的反应是边编边学?还是从编(辑)中学?《编辑社会学》再版时,先生改署“路石”。我琢磨着他是甘做铺路石?但我一直没有当面请教过他。我知道,张老师退休后先后被《中山大学学报》《史学月刊》《河南文史资料》《河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和河南省新闻出版局聘请为审校和质检人员。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都是编辑。
1996年我写《如法师》一文时,刚由郑州调到北京,工作尚未有太大负担,在文章结尾故做轻松:“如法师是一种境界,师如法则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近几年,我啃了一些知识社会学书籍,初悟知识社会学、社会知识论有望提供编辑学的理论基础,并有望带来编辑学研究的更大突破,期间总想起如法师,也更多地理解了他30多年前探究的意义,因而很想再向他求教。遗憾的是我几次登门拜访,他已患重病,我不想让他再做这些沉重的思考,便没有启齿。而今,与老师已天人永隔,讨教的愿望永远无法达成了。在某些具体的人事上,知识和社会就是如此绝情:共存社会未必能共享知识,能共享知识时,又不能共存社会了。

